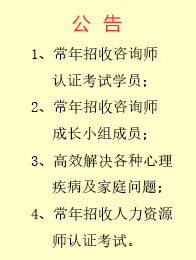明悦心理

让我们先来谈谈语言这个工具吧。首先,婴儿期心理与成人不同,通过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,我学到了触发儿童自由联想的路径,并借由这些联想抵达他们的潜意识。儿童心理学的特点,已经为我打好了借由游戏玩耍进行分析的基础。在玩耍和游戏中,孩童可以用象征的方式,表达他们的幻想、愿望以及真实经历。儿童用他们不成熟的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语言进行表达,这与我们所熟悉的梦的语言如出一辙。只有通过弗洛伊德所教导的解析梦的方式,我们才能完全了解儿童的语言。然而,如果我们想正确理解儿童的游戏行为,以及分析时的所有其他行为,我们就不能单单注目于游戏本身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零散的象征意义,尽管这些象征往往吸引着我们的视线。我们仍必须将所有机制以及所有梦境中用到的表征方式都纳入考虑,而不能将个别元素从整体情境中抽离。早期儿童分析经验一再显示,单个玩具或游戏往往可能代表多重意义,我们只有在考虑更广泛的联系并考察整个分析情境之后,才能够推断和解释它们的意义。比如莉塔的洋娃娃,有时代表阴茎,有时代表从母亲那里偷来的孩子,有时则代表她自己。我们只有将这些游戏元素放在与孩童罪疚感的联系里考查,并将它们尽可能详细地解析出来,这样的分析才可能充分。在分析过程中,儿童总是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,常常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可言。他们一下子玩玩具,一下子玩扮演,一下子玩水,一下子剪纸,一下子画画。孩子如何进行游戏,又为何突然改变游戏内容,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表达游戏的内容,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有内在联系与规则,如果我们用释梦的方式进行解释,或许这些行为的意义就会豁然开朗。儿童常常通过游戏的形式,表达出他们刚刚告诉过我们的梦境,他们也会通过游戏表达出对梦的自由联想。因为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表达媒介。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游戏分析技巧,我们便能够从儿童分散的游戏元素中,找出他们的自由联想,这和成人在梦的分散元素中的自由联想如出一辙。对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来说,这些分散的游戏元素便是很好的指征;而且小孩在玩耍的时候也会讲话,这些话都是很真诚的自由联想,都很有价值。
令人惊讶的是,儿童有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我们的解析,我们甚至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他们乐于被解析。究其原因,可能是在他们心灵的特定层面,意识与潜意识的沟通相对容易,故而重回潜意识之路对他们来说要容易一些。解析往往能够产生速效,甚至意识层面都可能不知道它已经进行过了。通过解析,孩子能够重新开始被心理抑制(inhibition)临时打断的游戏,变换游戏的玩法,拓展游戏的内容,从而我们得以窥探他们心灵更深处的秘密。当焦虑消散,游戏的欲望重新恢复,与精神分析师的接触便重新建立了。当解析过程驱散了儿童产生抑制的心理能量,他们就会对游戏产生出新的兴趣。而在另外一些时候,我们也会遇到儿童的阻抗(resistance),无法让他们配合治疗,而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触及了儿童心灵更深处的焦虑和罪疚感。儿童在玩乐中所采用的不成熟的、象征性的表征(representation),与另外一套原始机制相关。在游戏中,儿童往往用做来代替说。他们用行动替代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,这就意味着,在分析时让他们“用行动表现”(acting-out)是何等重要。弗洛伊德在《一个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案例》一文中说道:“对神经官能症儿童的分析显然是可靠的,但素材上却不会那么丰富;有太多语汇和思想可以借用在孩子身上,但即便如此,我们可能仍然无法抵达他们意识的最深层。”如果我们将成人精神分析的那一套方法照搬照抄,那么很显然,我们是不可能进入儿童意识最深层面的。而不管是儿童研究还是成人研究,只有触及了这些层面,精神分析才可能成功。但是,如若我们深谙儿童心理学与成人心理学的区别(主要表现在:儿童的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疆界比较模糊,最原始的冲动与高度复杂的心理过程相伴相生),如若我们准确地抓住了儿童的表达模式,那么儿童分析的缺点与困难都会迎刃而解,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可以对儿童进行精深的分析,正如我们在成人身上做到的那样。在儿童分析中,我们很容易通过儿童的直接表达,重回儿童的经历与他们的固着(fixation),而在成人分析中,我们只能通过重新建构才能获得。
1924年在萨尔茨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里,我提出一个观点,即在任何形式的游戏活动背后,都隐藏着儿童自慰幻想的释放过程。这种释放过程是以持续的游戏动机展现的,并表现成一种“强迫性重复”(repetition-compulsion),它构建了儿童游戏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升华作用(sublimation)的基础机制。游戏中存在的抑制即来自于对这些自慰幻想过于强烈的压抑,由此,儿童生命中的想象力也被压抑了。与自慰幻想相关的是儿童的性经验,儿童在游戏中找到了表达与发泄的途径。这些再现的经验中,原始场景(primal scene)是非常重要的一幕,占据着早期分析中最醒目的位置。通常我们只有在做完大量分析之后,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将原始场景和儿童性趋势揭示之后,我们才能够获得儿童性前期经验和幻想的表征。例如,四岁零三个月的鲁思由于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,在很长时间里处于饥饿的状态。于是在游戏时,她把水龙头称作“奶龙头”。她在游戏中解释说:“奶要流到嘴巴(下水道的口子)里去了,但基本上流不进去呢。”她在数不清的游戏和角色扮演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中,显示了她未能被满足的口腔欲望。例如,她总是宣布自己很穷,只有一件外套,没有东西吃等等,这些当然都和实际情况不符。
另一个例子是六岁大的厄娜,她是一个强迫症患者。她的神经官能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如厕训练造成的。在分析中,她很具体地向我展示了她的经历。例如,她让一个玩具娃娃坐在积木上,把其他仰慕它的娃娃排成排,看着它排便。然后的游戏中她还是玩同样的主题,但这次我得加入她的游戏。我得扮演成被屎弄脏的婴孩,她扮演妈妈。一开始,她对孩子是赞赏并爱护的,可不一会儿她就变了,变成了一个愤怒而严厉的母亲,开始虐待她的孩子。通过这个游戏,她向我描绘了她童年早期的经历与感受,那时她刚刚开始如厕等训练,她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,她失去了曾在婴儿时期拥有过的丰沛关爱。
在儿童分析中,我们不能因为儿童的强迫性重复行为,而将他们的外在行动和潜意识幻想看得太重。儿童固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喜欢用行动表现(acting out),而成人也常依赖这原始机制。他们在分析时获得的愉悦,为继续治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刺激,虽然我们得明白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。
当分析开始后,小患者通过解析已经消解了部分焦虑,于是他体会到一种放松感,促使他继续接受治疗,这往往是在最初几次治疗后就出现的。因为他们其实原先并没有被分析的内在需要,这种放松感让他们领悟到分析的作用与价值,于是有效的治疗动机产生了,正如同成人了知自身患病需要治疗一样。孩童的领悟能力证明了他们其实能够与现实相联系,不符合我们先前对这些小小患者的期待。关于儿童与现实的关系,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。
在分析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观察到儿童对现实的理解,一开始是很微弱的,而后随着分析的进行渐渐增强。例如,小患者开始能够区分假扮的母亲和真实的母亲,他也能够区分玩具弟弟和真实的弟弟。他会坚持说,他对玩具弟弟做这做那都是假的,他还是很爱真实的弟弟的。只有在战胜了强烈且顽固的抗拒心理之后,他才会理解他那些攻击行为其实针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对象。当这个幼小的孩子领悟到这一点,他其实已经向适应现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我三岁九个月的小病人楚德,在仅进行了一次分析之后便随母亲出国去了。六个月之后,她回国继续跟随我治疗。当时,促使她谈论旅途的所见所闻着实花了些时间,谈起来时她也只聊了和她梦境相关的那部分:她和母亲回到了她们在意大利去过的一家餐馆,服务员没能给她们红莓酱,因为红莓酱用完了。通过此梦的解析,加上其他一些现象,我们可以知道她还未从断奶的痛苦以及对妹妹的嫉妒中恢复过来。虽然她向我报告了各种显然无利于分析的日常琐事,还反复提及六个月前第一次分析时提过的细节,但唯一让她提起旅行的原因,是一次挫折事件,该挫折事件与分析情境中的挫折体验密切相关。除此之外,她对谈及旅行毫无兴趣。
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往往不能够接受现实,因为他们不能忍受挫折。他们否认现实,以此来回避现实的伤害。他们未来能否适应现实,最基础的、起决定作用的一点,要看他们是否能适应俄狄浦斯情境带来的挫折。在幼童身上,坚决拒绝接受现实(往往伪装成顺从与适应),其实是神经官能症的一个指征,它和成人患者逃离现实如出一辙,仅仅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。所以,早期分析的结果之一,就是能够帮孩子接受和适应现实。如若能成功达到这个目标,且不谈其他收获,仅教育方面的困难就会减少,因为孩子已经能够忍受现实带来的挫折了。
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,儿童分析中的方法角度与成人分析有不少差别。我们走了一条横穿自我的捷径,通过将自己置身于孩子的潜意识中,并由那里起步逐渐接触他们的自我。幼童的自我较弱,所以他们的超我所带来的过度压力比成人更厉害,我们要通过减少这些压力,来强化儿童的自我,并帮助他们的自我发展。